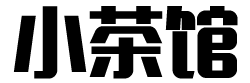--灵感源于之前毛毛说她像女侠。
--这篇文章送给每一个喜欢墨香铜臭的朋友,你们喜欢的人温柔且强大。
天真永不消逝,浪漫至死不渝。

壹.
我是个开茶馆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茶馆开在这么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正如外人所说,我开的这茶馆就不是给人喝茶的:
建的时候倒是踌躇满志,从各地采集了茶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废寝忘食地研究,一开张便知道玩脱了——建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选的地方不好。
我当时并不觉自己这间小茶馆开得有什么不妥,难得遇到几个建议我把它开到街头的茶客,我总是嘴上连声应着,心里暗暗不平:
凭什么?街上多吵啊,你喝茶不要氛围?
我觉得这么开没错,可它的生意就是惨淡到门可罗雀。
年轻人总是有一股宁可错到底也不肯回头的倔劲儿,我承认。当时无论是谁劝我把茶馆换个地方开我都不会听,因为我就是要犟着那一口气:
我挑的茶叶也好、泡的茶也好,都是罕见的上上品。
我不信我熬不出头。
就这么过了风平浪静的三四年,每天重复着挑拣、晾晒、冲泡的过程,我不厌其烦地和各色各样的茶叶打交道,披着一身茶香早出晚归地采集茶种。
偶尔有一两个愿意驻足停下的客人,我就会静静地给他们沏一壶龙井。
一切平静消失在她破门而入的那一天。
那天我刚采完茶叶回来,挑着满满两筐叶子杵在门口,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位扶着门框笑得灿烂的客人:
一袭黑衣,右手执剑,素白的斗笠边缘浸染着尘土和雨露的气息。
她冲我挥挥手:
“掌柜——一壶碧螺春。”
贰.
那是我第一次给人沏除了龙井以外的茶。
在我为数不多的客人中,她是唯一一个懂茶的人。
她支着下巴笑盈盈地看我倒茶,我注意到了她腕间隐隐约约的青黑血管,随口问了句:
“你是习武的?”
白色的云雾在壶中翻滚,她静静地看了半晌,才道:
“是啊,从小就喜欢。现在稍微带点儿徒弟。”
等到澄黄的茶水稍稍冷却,我挽起袖子替她把茶倒入杯中。突然,我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杯子的边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我下意识道:
“不好意思!我帮你换……”
她打断了我的话,挥了挥手,露出腕间浅蓝色的云纹:
“没关系。”
过了一会儿,我把视线收回到杯上,看着沉在杯底的茶叶,忽地冒出了一句:
“碧螺飞翠太湖美。”
我本就是自言自语着玩玩,也没指望有人能回答自己,哪知刚刚端起茶杯,对面忽地传来了一声轻笑:
“新雨吟香雨水闲。”
她笑盈盈地对上我吃惊的眼神。
那个黄昏,我的整个世界仿佛都化作了一抹斜阳,映在了她晶亮的瞳仁中。
我在她眼中看到了光。
我们对视了几秒,蓦地相视而笑。我推开那扇许久未开的木窗,让窗外带着水汽和青草气息的晚风扑进馆内。风声呼啸,我不顾被吹得有些散乱的头发,哑着嗓子大声问她:
“我能跟你走吗?!”
她向我伸出了手:
“好啊。”
叁.
我跟着她走出了茶馆,并且很长时间没有再回来。
临走前,我把茶馆托给了手下的小徒弟,嘱咐他帮我照看好馆内的一切,背着轻装踏上了一条她引着我前行的路。
她叫什么至今为止我仍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我一般会叫她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她自己一次聊天中无意间告诉我的,她说比起别的,她似乎还是更喜欢这个称呼。
我成为了她门下弟子中的一员。他们在深山中修行,时机成熟便会出世历练,从此隐入尘世,不再归山。
不过我除了习武外,还经常和她一起品茶。
一日训练,我早早地到了校场,身旁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今天起得挺早嘛。”
我认出了这是前几天主动带我参观这里的一位师姐,也笑着回答她:
“多谢师姐。”
一道白衣身影忽地闪现在校场正中央,我看见女侠冲我眨了眨眼睛,“铮”的一声,佩剑出鞘,锋利的剑锋直指我额心。
我自然知道她不会真打,草草提剑伸手格挡,却被几近生猛的力道震得手臂一麻,忍不住抱怨道:
“练习而已,用不着那么使劲儿吧?”
哪知她面上浮现出了近似于困惑的表情:
“我很用力吗?”
我笑着轻轻推了她一把:
“实力太强。”
习武练剑至黄昏,等众人七七八八都散去休息了,我提着一次外出她编给自己的小竹篮收拾了东西去山头找她。
平旷的草地另一头是断崖。
橘红色的落日在我们脚下的滚滚云海边缘徘徊,我们就着霞光泡了一壶龙井。
她支着腿斜躺在成片的芳草上,白衣如同天边的云浪层层铺开在大片的青绿之中。
我问她以后打算怎么办,她抿了一口茶,感慨道:
“就保持现在这样,我觉得也不错了。”
虽然她收徒收得不多,我的生意不温不火,但是我们都觉得维持着现在这种岁月静好的生活,偶尔做一做喜欢的事情,也足够了。
我曾自私地希望生活一直会是这样的。
但是,之后发生的一切无一不残忍地向我宣告着——
不可能的。
肆.
她入了江湖。
那天她带着门下优秀的弟子与我一同前往武林界举办的比武盛会,那些孩子同人过招所用的一招一式都是规矩得不能再规矩的基础招式,既不算锋芒太甚也不算唯唯诺诺拿不出手,一天的轮赛结束,她笑盈盈地挨个拍拍他们的肩,转身揽着我的肩同我一起上了街。
我听见她在我身旁喋喋不休,兴致盎然地扯着我的衣袖给我指这指那:
“你怎么不说话啊?这是那家很出名的酒馆,之前跟你讲过的。”
我转头问她:
“你喝酒?”
她哈哈道:
“没有没有,我不喝。喝酒坏事儿。”
我说:
“可是那些人,她们都喝酒啊。”
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些人”是指江湖上那些比较出名的侠客,摆摆手,把腰间的白玉笛子解下在指间转了几转,道:
“那是她们。她们喜欢练武时喝酒助兴,不过我不爱这么干。”
我了然。
在街上晃悠了一个时辰,天色渐晚,我们起身准备回到大会规定的住处。
刚刚走到客栈门前,忽地见远方“噌”地燃起一层火浪,接着只听一片铮铮的佩剑出鞘之声,夹杂在混乱的人声中直刺人的耳膜。
我认出了那是她独创授予弟子的一道引火咒,当即向她投去了惊异的目光,却见她也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对视一眼,不约而同起身地赶向火光燃起的地方。
等赶到时,明火已经熄灭了。
一群她带过的弟子们额角挂着血,在众人的簇拥下笑着应着什么,见她出现,纷纷向旁人介绍:看,这是我师父。
我能从她眼中看出带着几分迷惘的惊喜。
从他人口中东拼西凑了半天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街上喝茶的时候,大会现场忽地涌入了一批类似于魔教组织的可怕人物,在场的竟没几人能拦住这些人肆意打砸,可就在这时,那些随我们下山的孩子用了她的引火咒,一击即中,把这些来路不明的人给活活逼到绝路上,生擒了。
因为座下子弟使用的咒术都由师父亲手所创再传授的,这几个孩子一向他人说出了师父的名字,原先她在山中幽静得仿佛世外桃源的小仙境忽地变得门庭若市。
那天黄昏我们照例坐在山头喝茶,不过这次耳边不再是清越的鸟鸣,而是喧嚣纷嚷的人声。
她躺在我身旁,看着山门口堵着的一长串人,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问道:
“你高兴吗?”
她似是有些纠结,敲了敲太阳穴,长叹一声:
“有人愿意和我学肯定高兴,不过人一多了,我怕出事。”
“我怕出事”这句话本是随口说说,我们谁也没把它当真,哪知数日后的一个清晨,这句话竟一语成谶。
伍.
她越来越出名了,而我是和她一起下山买茶叶时发现不对劲的。
我们身旁的两名茶客虽然谈论着她的名字,但似乎不是什么好的话题。我怕她听见了受不了便把她支去结账,自己装作看风景,倚着门偷偷听着。
一人连声抱怨道:
“她把我们掌门的所有风头都压下去了,这让人有什么活路?!”
另一人又道:
“光说又没用,有这时间不如想个实质点的方法让她从江湖滚出去,反正是个二十出头的丫头,随便用什么法子击几下不就成?”
他们言语的走向越来越不堪,我愣在原地,说不清楚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人用这么恶毒的语言形容她,说到底都是初入江湖的新人,有点才华的不在少数,凭什么专门骂这一个?
就因为她收的徒弟越来越多?
那也是她自己凭本事收到的,你们又凭什么把她逐出江湖?
诚然,江湖不缺这种初出茅庐便显露头角的新人,但是如果每一个都被你们的污言秽语逼走,那江湖还剩什么?还有发展余地吗?
难道有实力有才华都是错的?
这些话我想着想着无意间就说出了口,那两人侮辱人正上了兴头,猛地被人打断,一人当即起身,抓起酒壶“咣”一声砸碎在我脚边:
“你他妈凑什么热闹?老子骂的就是她!”
我把手按在了剑柄上。
另一人当即嗤笑道:
“看吧,我说的。她带的小贱种就只会动不动上手打人啊。”
我用几近怨恨的目光死死瞪着他们,佩剑悄无声息地出鞘了半寸。
可这半寸又被人按下去了。
我看见她站在我身后,面色苍白,按着我手背的那只手冰凉至极。
她对我说:
“不要和别人打架。走吧。”
上了山我才发现,她哆嗦的那只手抓着的茶叶,买错了。
第二天,山门口就多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让弟子们潜心修炼,不要打扰别的门派。
此后,每当这告示被风刮落或是被雨水浸湿时,她都会重新写一张,架着梯子,自己亲自把写好的告示再挂上去。
由于她错买的那包糟糕透顶的茶叶,我们好久都没有再一起喝茶了。
陆.
她们最终还是下手了。
她们把我们生活着的世外桃源,生生变成了一片混乱不堪的角斗场。
那日清晨,我下山买茶,却见大批的修士举着剑义愤填膺地往她所在的山头冲去,我抓住一人,厉声问道:
“你们要干什么?”
那人不耐烦道:
“松手!我们掌门被她座下徒弟所伤致残,少了一条手臂,我们要替她讨回公道!”
我呆呆地愣着,看着他们浩浩荡荡地举剑上山,一时间僵直了身体。
过了不知多久,我才动作木然地买了一包茶叶,转头赶向了受伤的那名掌门所在的城府。
结果你猜,我见着了什么?
那名传闻“残疾”的掌门,正在校场上乐呵呵地调教自己未出世的一批徒弟。
她的生活平淡无奇,而另一边的我们所居住的山头,蓦地响起了一片兵器撞击的巨响。
这一切都是因这位粉衣掌门而起,但她却乐在其中,享受着由他人痛苦所换来的欢愉。
可恨啊。
我赶到山上时,人已经七七八八散了不少,我推开几个碍眼的修士,跌跌撞撞地奔进了她的书房。
她正看着窗外发愣。
我看了看她手肘边翻了一桌的墨水,视线上移,依稀认出了她手中的那张纸上是什么:
一封道歉信。
还用朱砂印了手印。
想必是本想寄出去,却不料他们会有这么一出攻上山头的好戏,连信鸽都抓不住了。
我沉默着,半天才道:
“我去了她那里。”
她这才缓缓转过身,声音极轻地道:
“她怎么样?如果有人因为我受到了伤害,我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看着她眼下的淤青,话到嘴边突然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可最终我还是告诉了她这个残酷的事实:
“她没有受过伤,这件事本来就是她故意拖你下水的。”
一片死一般的沉默。
过了好半天,我才听到了一声沙哑的“为什么”。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柒.
那一天是四月十日。
那天过后,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面无表情,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和我喝几次茶才会露出我们初见时那般明朗的笑容。
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帮她解脱。
搅进了这趟浑水中就再也摆脱不掉了。
她明白,我也明白,我相信她们也明白。
因为她们要把她和她的一切都推入地狱。
那天我本想陪她坐坐聊会儿天,却听她罕见地提了一句想喝我泡的碧螺春,我大喜过望,主动提出帮她去买。
可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又一次没能在混乱中站在她身旁。
这一次我看着与上次同样义愤填膺的人群冲上了山,其中还有很多我眼熟的同门,突然就懒得再问他们为什么了。
能有为什么?他们伤害别人又不需要理由。有时候只需要一句也许根本不是事实的话,就能让他们从六艺俱全的风流人士堕落成半人半鬼的废物。
我转头买了三包龙井。
回山时,我看见她静静地立在屋顶上,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山脚混乱的人群。
说来可笑,明明是她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奇幻而又瑰丽的仙侠世界,而我的引路人自己却深陷其中,在晦暗不明的人世间饱受着没有由来的谩骂与羞辱。
我进屋沏了杯茶,翻上屋顶小心翼翼地端给她:
“三天没吃饭了,喝点东西吧。”
她用一种迷惘至极的目光呆呆地看着我,好半天,接过茶一饮而尽。
“你的那个大师姐走了。”她低声道,“回头亲手想要用我教给她的方式杀了我。”
一个不小心,瓷玉的茶杯自她干燥的指间滚落,“啪”一声碎在了大堂高挂的牌匾下。
半晌,她回手抓住我的肩一头撞了上去。
我问她:
“以后还想接着在江湖待下去吗?”
她苦笑一声:
“看情况吧。”
八月三十一日,这次的茶喝得并不愉快。
捌.
意外总是成双出现。
其实也不算意外,意料之中。我们的世外桃源被人烧了,就在那天不久之后。
三栋木楼被生生炸毁了两栋,火花飞溅,木匾自檐下跌落,摔得四分五裂。门派下忠诚的弟子奋力反击,放眼望去一片腥红。
那一天,她才刚从前两次的打击中缓过来,勉强答应了和我一起下山买茶叶。
我们上山的时候,那些人正在冒着黑烟的废墟上狂欢。
他们足足有乌压压的一片。
我看见她垂下头,攥紧了拳,一掌击地,开启了山上的守护结界,将这些妖魔鬼怪从山上逐了出去。
我发现手中的茶包不知何时落在了路上,便和她说了一声,一面让她一个人静静,一面下山找落下的茶。
等我找到灰土中的茶包,起身准备回去时,却见山头“砰”一声爆出一道红光,我心头一悬,抓着茶包拔腿就往山上跑。
中途摔倒在血泊中再爬起来时,我尝到了齿间腥甜的味道。
等我匆匆赶到时,却见她指间夹着一张冒烟的符,用力抛向空中,“砰”一声炸成了一道红色的火花。
刺目的光芒在黑夜中将她的脸照得阴惨惨的,我伸手抓住她手腕,却被她一把拽倒在一地废墟之间。
地上的血都是热的。
我起身,从唯一一栋幸存的楼中取出了茶炉,沉默着点了火,将沾着血和灰的茶包拆了外面的牛皮纸抖进炉中。
见她一个人坐在血泊里哆嗦,我解下披风轻轻搭在她身上:
“进屋吧,暖炉能用。”
我看见她的眼中缓缓地淌下泪来,泪水在她沾满了鲜血和尘土的脸颊上冲出了一道雪白的痕迹。我抽出手帕替她擦了擦脸,道:
“别哭了,他们不值得。”
她抹了把脸,主动把炉中烧得半开的茶倒进杯中,笑了笑,把两杯茶中的一杯塞进目瞪口呆的我手里:
“没事,不是因为他们。他们骂得再狠都没关系,我只会因为爱我的人感动。”
我们相视而笑。
这是我们喝过最有意义的一次茶。
我问她还会不会再传授武术,她挥挥手道:
“当然。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教下去的。”
过了一会儿,她歪头笑道:
“你泡的茶挺好喝的,下次试一试把店开在街心吧。肯定会出名的。”
翌日,我从一片废墟中醒来时,发现她不告而别。
同门的师兄弟纷纷来问我她会不会再回来,我看着身旁茶壶中早已冷却的茶,轻声道:
“会的。我相信她。”
玖.
我听她的话把茶馆开到了街心。
果不其然,刚刚开张几天,一次偶然的机遇使我碰上了城中一位开茶庄的商人,于是我的茶在一夜间风靡全城。
一时间来的茶客几乎踏破了门槛,我招了几名学徒细心带了几年,将城中的这间小茶馆托付给了他们,自己回到了我们初遇的那间郊外小屋。
细细地拂去窗边几年积攒下来的灰尘,我坐在当初我们喝茶的那张木桌前,倒了两杯碧螺春。
几月过去,元旦将至,我起身到自己城中的茶馆和亲朋好友们过年。
除夕夜,皑皑白雪中飞来了一只腿上绑着红色风铃的信鸽。
我打开窗将它托在掌心,解下了它腿上的风铃和竹筒,从里面抽出一张缀着红梅的信纸。
我把纸展开,看见了上面有一行力透纸背、笔锋流畅的字:
“除夕快乐,年夜饭吃了吗?”
我迎着寒风勾了勾唇角。
隔着漫天飞雪,我看见了她在天边微笑。
拾.
我回到郊外的茶馆时已是春暖花开。
我远远地看见自己屋顶的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了斑驳的虹色光点,迎着光,我看见了茶馆的烟囱向外飘着袅袅炊烟。
我不禁加快了脚步。
推开门,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听见身后的响动,那个伏在炉前看着火的白影立即直起了身,冲我笑了笑:
“客官,要不要来一壶碧螺春?”
我揉了揉眼睛。
这次,没有人再紧追着她不放了。
她在昔日废墟遍布的山头栽了花,成片的花海在焦黑的土地上蓬勃生长。
她兴致勃勃地牵着我去看山头如火一般赤红的花海,我看着她蹦蹦跳跳的身影,问道:
“你还会走吗?”
她回头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不会了。”
我们像十几年前一样仰面倒在花海中。
她支着腿,眯起眼睛看着天边翻滚的云海,我低头看着她。
真好啊。
经历了这么多,归来却仍如少年般质朴纯真。
我听见她喃喃道:
“……以燎原之势重生……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迎着霞光,我望向了身后赤红的花海。
她纱衣的那抹素白在红色的海中层层叠叠地伸展开来。
推荐文章:
孕妇能喝玫瑰花茶吗
经期可以喝茶吗
玫瑰花茶一次泡几朵
玫瑰花茶的泡法
恋恋奶茶小铺配方
黑茶的功效与作用